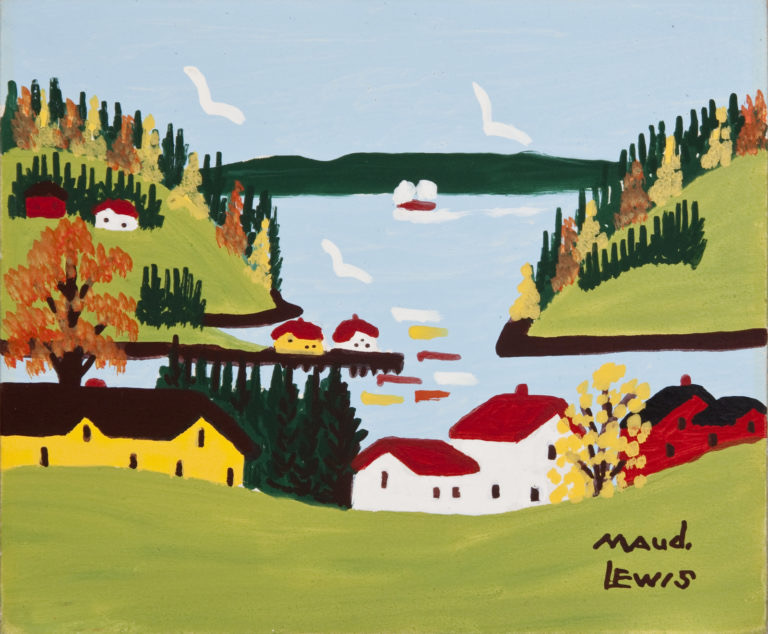
3-39 凡人
——宗教能给人什么?
【我在此地的向导是一个名叫Nyein的女孩。她自称十二岁,但看起来比立雪瘦小得多。今天她带我去山上走访,我们走了四个小时上山。她穿一双底快要磨透了的塑料人字拖,山路走得比我都快。中午她带我到山间的一户人家,站在门口与人商量,那户人就留了我们吃饭。我坐在门口,看着他们一边做饭一边和Nyein聊天。看得出物质条件有限,房子是传统的竹和茅草盖的单间,屋顶很低(对我来说),采光不好,也没有电,烧的是柴灶。他们为我加了菜,矮矮的小桌子几乎摆满了。但是仔细看过去,全都是清炒南瓜秧、南瓜秧炒鸡蛋、南瓜秧鸡蛋汤,每个盘子里翻来覆去排列组合的都是南瓜秧和鸡蛋。南瓜秧里还有已经长老了的南瓜叶,茎上的毛刺剌舌头(依旧鲜甜)。鸡蛋一共只有两个,他们不停地打手势让我吃。饭后我问Nyein需要给主人多少钱,她说不用给钱,因为我们是客人。我很惊讶。我给了他们两美元小费,他们很开心,欢迎我再去。我的本意是希望多给一些,但唯恐得罪Nyein,因为我每天也只给她两美元。我带够了钱的,不用担心我。只是此地物价很低,而且你教导过我,斗米恩升米愁。我也不希望被当地人视作冤大头,尽管这份犹豫和提防让我自己并不舒服。(我在仰光转车时为你买了一块手工挂毯,当时没有告诉你花了一百二十美元,因为我觉得很漂亮,值得价钱。但上次去密支那,我发现类似的挂毯在这里只要二十美元。我是不是很傻?)】
【有一次我夸Nyein的英文说得很好。这种好不是基于词汇量,而是她应用外语的能力。她介绍说为了找到工作,她去年跟同乡的另两个女孩结伴搭车去密支那,跟定居在那里的一个同乡学了两个月。那位老师专门在家教英语,许多想要从事旅游业的缅甸人前去学习,因为旅游业几乎是最赚钱的生意了。我们一路上在景点见到的孩子们都有令人惊异的领悟力,甚至在我和同伴刻意用德语讨论他们的售价时,那些七八岁的孩子都能捕捉到我们语气中的倾向,追着我们用英语混合着听到的德语词劝说购买。我们只能为之折服,买了两美刀的明信片,自我安慰在北美的博物馆商店也要类似价钱。我不免会想,如果这些孩子得到更好的基础教育,而不是为了讨生计日复一日地追着游客推销千篇一律的小商品,他们可能拥有什么样的未来?哪怕内比都路灯的电费节省一半,都足够养大他们进入大学了。】
……
【我这些天一直在理解公共建筑对人民精神状态的影响。有一次我们也聊过,你说你家乡的文化宫里最受人喜爱的不是任何功能建筑,而是榕树的树荫。在加拿大,我们去图书馆和社区中心;在缅甸,尤其一些小的村落,人们在寺庙里聚集。】
【仰光是个很有意思的地方,穿过市区时能看到佛教、伊斯兰教、印度教建筑几分天下,泾渭分明,各不相让。往北部走,佛教的影响力渐渐增大。这次在曼德勒,我们在街头看到僧人化缘,捧着钵,长长的一队,所有平民都自动驻足回避。路边的人家提着电饭锅内胆等在路边,给每个钵里盛一勺饭,就这样挨家挨户慢慢行进过去。当地人很虔诚,家家户户都愿意尊重、供奉僧侣。我们造访寺院时,我看到小学组织孩子在那里参观学习。信仰是这样传递给下一代的,但这样是对的吗?因为成人如此,就给未成年人灌输一种宗教思想,而不是在他们有了独立思想后再自行选择。历史上近乎都是这样。但这样对孩子是合适的吗?】
【此前我在驻地的随行翻译Nyein是个小女孩,我们虽然走访了一些寺庙,但当地人和僧侣都很客气。也许因为他们的英文水平有限,从没有人同我讨论过宗教信仰。这次在曼德勒,租车的当地司机主动要给我们做翻译。他是个略显油滑的年轻人,眼里有直白的、看待冤大头的嘲讽。尽管他在无信仰者面前有种微妙的优越感,但我在直觉上,不认为这是任何宗教的信众对待外界应持的态度。我在food bank和thrift store共事过的那些天主教的爷爷奶奶们不是这样的。在寺院里,招待我们的僧人介绍了一些我觉得很笼统的东西,总而言之,出家就是“放下一切”?他们说,皈依就是不再拥有身外物,他们指着我的包,相机,婚戒,还有同伴里的一个师姐;我们这一行中有一对情侣,他们指着她对她的男朋友说:“还有她。”虽然师姐笑而不语,但我坐在旁边为她感到了冒犯。】
【从密支那到曼德勒的一路上,主要目的地几乎都是宗教建筑,但他们对女性有不同程度的拜访限制。像是不允许女性触碰佛像、上供金箔,有些不允许进入内殿,甚至有的地方连上山的台阶都禁止女性踏上一步。过去我印象里只有穆斯林有这么多性别限制。虽然那是一种民俗,或许在世界各地不同的文化里都有,但还是使我不舒服。虽然我并不信仰天主教,在加拿大这个天主教国家——哪怕说他们的礼貌是一种虚伪的友善吧,至少他们没有给过我这些负面感受。如果你在这里,对金子的喜欢可能都不足以让你欣赏被金箔贴成巨大的一坨、看不出原本轮廓的佛像。】
……
【今天我们抵达蒲甘,途中收到教授邮件,称政府上门叫停项目,要审查我们的设备和资料。我们几个出来玩的学生需要在蒲甘停留等待审查。希望不会太严格。我不是长期人员,电脑也带在身边,没有作为项目资产被统计过。也没什么隐私文件,但如果被他人翻看还是会不舒服的。蒲甘作为旅游发达的地方,民宿的条件很不错,冷气很足。外面三十六度,连树荫都很少。加上不必赶明天回去了,大家一进到房间就泄了气,没有人想再出门了。但是我很想你,很想你。如果不是因为时差,现在就想听到你的声音。】
周星原戴上他被汗浸透还未干的帽子,背上书包和相机,往烈日下走去。三十六度暴晒着,下午两点的蒲甘平原,黄土路上人影全无。他不想在房间里休息避暑。身边没有方荼,浪费时间则毫无意义。
前台拿来的地图上,标示在正南方向有一个遗迹,步行约需一小时。他打算去看看。蒲甘地势平坦,但作为一片古迹,道路只有几条黄土大道穿插其间,和棋盘格的宁古塔并不相同。
说古迹也不尽然。近年为了发展旅游业,也许为了乘热气球时有更好的俯瞰视效,当地在两千多年历史的真古迹间加建了一批急功近利的简陋水泥塔;2016年地震后,一些原本就缺乏修缮的古塔坍塌,衬得水泥塔更显得滑稽。离开游客往来的民宿、酒吧区域,大路以外,走进历史和自然的天地之间,这种违和尴尬的感受才渐渐淡去。
走着走着,周星原却感到了另一种不对劲:纸质地图上、本该出现的岔路口始终不见。他离开道路,走向塔丛。
“请问有人吗?”他看见一个敞开的门洞。
里面缓缓走出一位穿僧衣的老人。“你好,年轻人。你迷路了吗?不是迷路的话,不会有人来到我这里的。”
周星原举着地图:“我想是的……”
老人打手势示意他进去。“外面太热了。进来坐一会吧。”
周星原跟他进去,在台阶坐下,接过老人给他的水碗一饮而尽。“您的英语说得真好。”他从未听当地人、更不用说老人或僧人讲这样流利的英语。
老人从旁边的旧塑料桶里给他添水。“我在澳大利亚生活过很长时间。你是中国人吗?中国我也去过。”
周星原吃惊:“您是本地人吗?”
“我是的,我就出生在这里。”老人始终面带从容友好的笑容,坐在对面同他闲谈起来。
能这样顺畅地沟通,令周星原大为振奋。
老人从小在蒲甘出生长大,投身佛教。少年时在仰光进入大学,深入学习巴利语:上座部佛教以巴利语为圣典语言。其后他在大学做研究、去澳洲长期任教,去世界各地包括北京都参加学术交流和宗教活动。直到近年才落叶归根,回到蒲甘生活;如今他已年近九十了。
周星原立刻意识到,他恐怕邂逅了一位学术大拿。
“我不知道我的疑问是否合适。我看到这里的民众都很虔诚,竭尽全力为寺院付出。僧侣会如何回报他们吗?像在中国,那些大乘佛教的寺院里,僧人会收取费用,为信众许愿、祝福等等。”虽然那些安慰行为在他看来也是敛财手段而已,但周星原的眼中,缅甸人民对佛寺的崇拜近乎被压榨:他看过衣裳朴素破旧的信徒往造像上贴金。宗教又能给他们什么?
老僧人笑着摇头:“上座部不做这些。民众的任何行为,是他们的个人行为。我们对他人没有要求,也无法回应他们的期待。上座部并不宣扬来世和轮回。”
在老人简练的解说里,为周星原揭开一个同他在缅甸的见闻中完全不同的宗教。不论信众和世俗如何理解看待上座部,在僧侣眼中,上座部佛教是无神论的。他们认为佛陀并不是神,而是一位哲学先贤。上座部僧侣的修行,并不求拜任何偶像,而是通过阅读、学习和冥想去追求更高的个人思想境界,去成为一个更理想的凡人。
